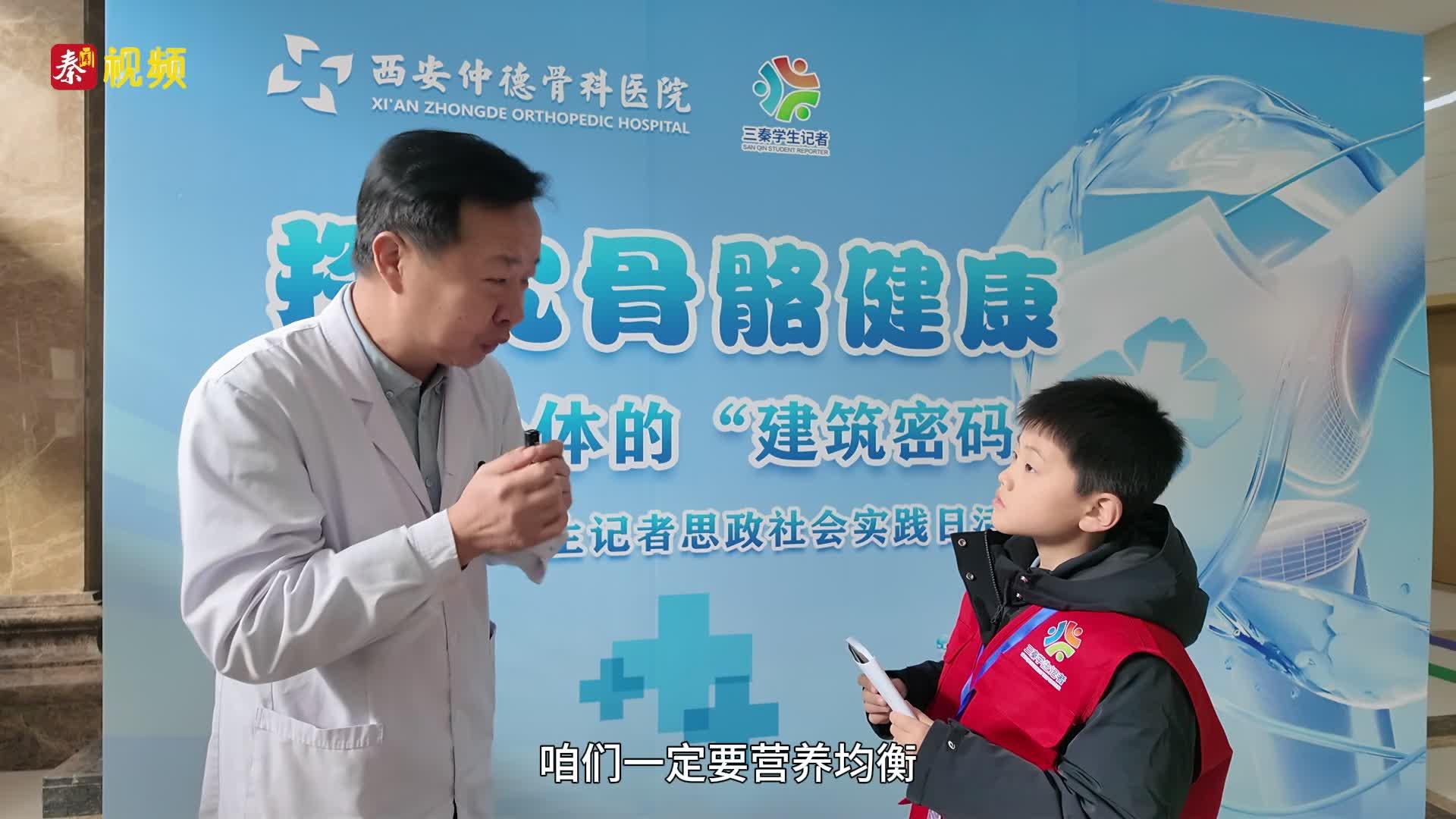北京互联网法院5月26日发布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审理的情况及典型案例,法院受理的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案件中,充值打赏类案件占比较高,达到75%,标的额最高的一个案例中,涉案金额高达61万。
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充值打赏的未成年人都是小学生,用父母的手机注册账号,充值游戏、打赏主播、看付费漫画等,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遇到哪些问题?法院又有哪些建议呢?

未成年人充值打赏类案件多发
且涉案金额较高
北京互联网法院副院长姜颖介绍,自2018年9月北京互联网法院成立以来,共受理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76件,当事人中年龄最小的受侵害者仅为5岁;8至16岁的有66件,16岁以上的为7件。从案件的具体纠纷内容看,主要集中于充值打赏、网络购物、人格权侵权等类纠纷。
姜颖:其中,游戏充值案件20件,直播打赏案件22件,其他充值类案件15件,充值打赏类案件占比达到75%。在充值打赏类案件中,原告多主张未成年人充值行为不发生效力并要求返还充值款。

姜颖说,充值打赏类案件涉案标的都比较高。
姜颖:游戏充值案件的平均标的额为84647元,直播打赏案件的平均标的额为69712元,金额最高的案件为某游戏充值案件,涉案金额高达61万元。
未成年人看直播8天打赏4万元
直播平台承担主要责任
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小学生小刘,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用父亲的手机号在被告运营的直播平台注册账号,仅8天的时间,通过微信充值4万多元,在直播平台上购买虚拟礼物、打赏,小刘的监护人以小刘的名义起诉,要求法院确认原告小刘在被告处的充值行为无效并判令被告返还充值款。
北京互联网法院少年法庭庭长孙铭溪:本案中原告系未成年人,其所进行的高额充值打赏行为与他的身份、年龄和经济状况不相适应。本案审理过程中,经法院主持,当事人达成和解,被告同意返还原告的充值款项。

案件审结了,但是法院的工作并未结束,法官指出,未成年人的年龄、智力尚不成熟,尚未形成理性消费的意识,在互联网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下,未成年人非理性高额充值打赏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而相关网络平台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孙铭溪:案件审结后,法院就审理过程中发现的被告平台在实名认证、未成年人身份识别、风险防控、主播监管等方面的机制缺失和管理漏洞向该平台发送司法建议,推进该平台完善注册、充值、打赏环节的身份认证机制,优化风险监测防御机制,加强平台主播的监管、培训、惩戒,构建未成年人内容建设体系。
建议父母等监护人提升自身素养
教育、引导未成年人合理使用网络
副院长姜颖指出,案件反映出,在网络娱乐消费领域,特别是网络游戏、网络直播领域,未成年人容易出现沉迷,而很多家长并未掌握孩子使用互联网的真实情况。
姜颖:在法院审理的涉未成年人网络充值、打赏案件中,未成年人多从简单接触网络游戏、网络直播开始,进而通过充值、打赏获得了更好的娱乐体验,后发展为大额充值打赏,个别未成年人甚至为其游戏账号购买了代练级服务。案件中绝大多数未成年人存在逃避家庭监管、规避平台认证措施的情形。

典型案例中,放假期间,小学生小张用母亲的手机,以母亲的名义注册某直播平台账号,在无需输入支付密码的情况下即得以在网络平台对游戏直播进行充值打赏,仅6天打赏1万多元。起诉平台后双方达成和解协议,而法院向小张的母亲发出了首份线上家庭教育指导令。
孙铭溪: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发现,涉未成年人充值打赏纠纷中,许多未成年人的家长存在自身网络素养不足,对个人电子设备或支付密码保管不当,对未成年人用网行为教育、示范、引导和监督不到位等问题。本案就是这样一起典型案件,法院发现上述问题后及时向张某的父母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督促其尽快提升自身网络素养,教育引导未成年人科学、文明、安全、合理使用网络。

疫情期间,很多中、小学生都在家里上网课,家长没有听到玩游戏的声音,以为孩子在安静地学习,可能真实情况并非如此,未成年人网络安全意识较弱,易受不良信息侵害。典型案例“软色情漫画充值案”中,初中生小王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内,持续充值付费浏览含有“软色情”内容的漫画书目100多篇,在造成财产损失的同时,也影响了身心健康发展。
副庭长颜君: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部分纠纷确实是在疫情期间学生用网所引发,反映出家长对孩子用网情况了解不足、监督教育引导不够、缺乏风险防范意识等问题。对此,建议父母等监护人及时了解孩子入网情况,对上网设备设置身份验证和青少年模式,妥善保管自身身份认证和账户密码等信息。针对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合理安排用网时间和内容,审慎挑选适宜未成年人使用的应用软件和终端设备,关注未成年人接触的网络信息是否健康。根据具体的需求设置用网时限,同时倡导家长加强亲子陪伴,引导未成年人使用网络学习知识,拓宽视野,提升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