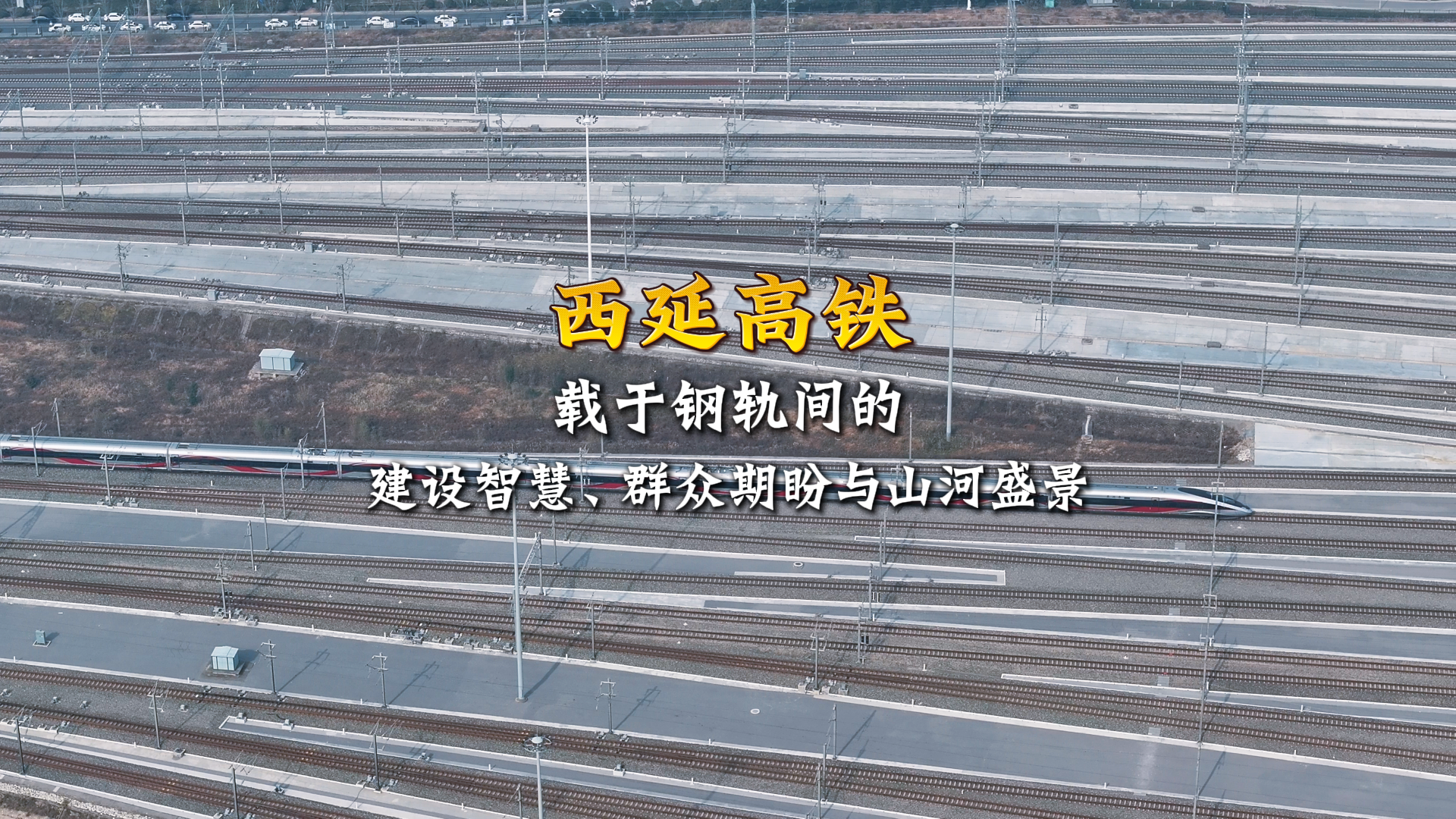作者:张瑾
医院急诊科的灯光,是二十四小时不眠的冷白色。它照着来往的担架床、急促的鞋印,也照着我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穿了一年又一年的护士服。日子像滴管里匀速坠落的药水,精确、重复,不可或缺,却无声无息地消失在看不见的尽头。每当夜深,消毒水的气味沉淀下来,一种庞大的迷茫便如潮水漫上心头:除了护士,我还能成为谁?我生命其他的可能,难道就被这四壁与孤灯,温柔而决绝地封锁了吗?

转变发生在八月一个明朗的上午。社区活动中心里,身穿红十字马甲的老师正在讲解急救知识。交谈中得知,他们来自西安市红十字应急救护服务中心,正系统化地培育应急救护力量。我才意识到,自己每日熟练使用的技能,并不只能困于医院的高墙之内——它们可以被专业地组织起来,像种子一样播撒到任何需要的地方。几乎没有犹豫,我报名参加了他们的救护员培训班。
第一堂课,我认识了亨利·杜南。一个人,一场战争,一本书,后来孕育成一个组织、一部公约,最终化身为遍及全球、拥有万千志愿者的红十字运动。他让我看见:一个人的力量或许微弱,但一份纯粹的善念一旦付诸行动,便能点燃星火,终成燎原。
那一夜,我久久难眠。我好像终于触到了那条隐约等待我的路。

接下来的四个月,生活的密度与宽度被悄然撑开。我完成了救护员培训,又在老师的鼓励下,迈向更具挑战的师资培训。讲台,成了我另一个“急诊室”。
在社区,面对好奇的孩子与担忧的老人,我把生硬的医学知识,变成他们听得懂、记得住的故事;在校园,望着少年们眼中戏谑渐褪、认真浮现,我仿佛看见一道微弱却坚实的安全防线,正在他们心里一寸寸筑起。每次课程结束,听到那句真诚的“谢谢老师”,或是发现有人开始下意识地观察安全出口时,一种前所未有的、饱满的成就感,便轻轻将我托起。
如果说技能的精进是支撑我的骨骼,那么在这里遇到的人与事,就是为骨骼注入生机的血肉。退休医生将毕生经验凝成口诀,企业职员牺牲周末只为多教一个人,长辈们认真记笔记的模样像重返课堂,更有无数平凡的志愿者,名片上没有头衔,却总出现在需要的地方。这种纯粹而热忱的氛围,像一场透彻的春雨,将我心中职业的倦意与淤堵,一点点冲刷干净。
我开始重新凝视身上这袭白衣——它不再只是职业的装束。当我走出医院,它依然可以是一面旗帜,引领我去照亮那些陌生的、可能需要的角落。

变化是无声的,却逃不过最亲近的眼睛。弟弟是年轻党员,一向以思想进步自居。一次家聚,我说起在红十字会的点滴:如何在公园里教人心肺复苏,如何在模拟救灾中搭建帐篷、疏散群众。他听得很静,然后说:“姐,说实话,看你现在这样,我有时觉得惭愧。你做的每件事都落在实处,心里总装着别人。这份实在,我得向你学。”
我望着他年轻而诚挚的眼睛,忽然明白:曾经我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总眺望别处的灯火。而今,我自己竟也成了一束微光——不耀眼,却足以照亮脚下的一小片路,甚至不经意间,把一粒种子播进另一颗向上的心里。
他的话让我确信:那粒关于责任与奉献的种子,已经落进土壤。会不会发芽,开出什么花,我不知道,也不必知道。就像当初照亮我的那束光,也从未要求我必须长成参天大树。
我只是循光而行,走出了自己的狭谷。然后,不自觉地,也想成为光。
急诊科的灯依然冷冷亮着,照见生命的无常与脆弱;而我心里,如今亮起了一盏暖而稳的灯。它照见的是生命的韧性、知识的能量,以及人与人之间最朴素也最坚韧的联结。
我不再问“我还能做什么”。
答案就在每一次伸出手的传递里,在每一颗被唤醒的、珍爱生命的心里。
这条路,我会稳稳地、热忱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