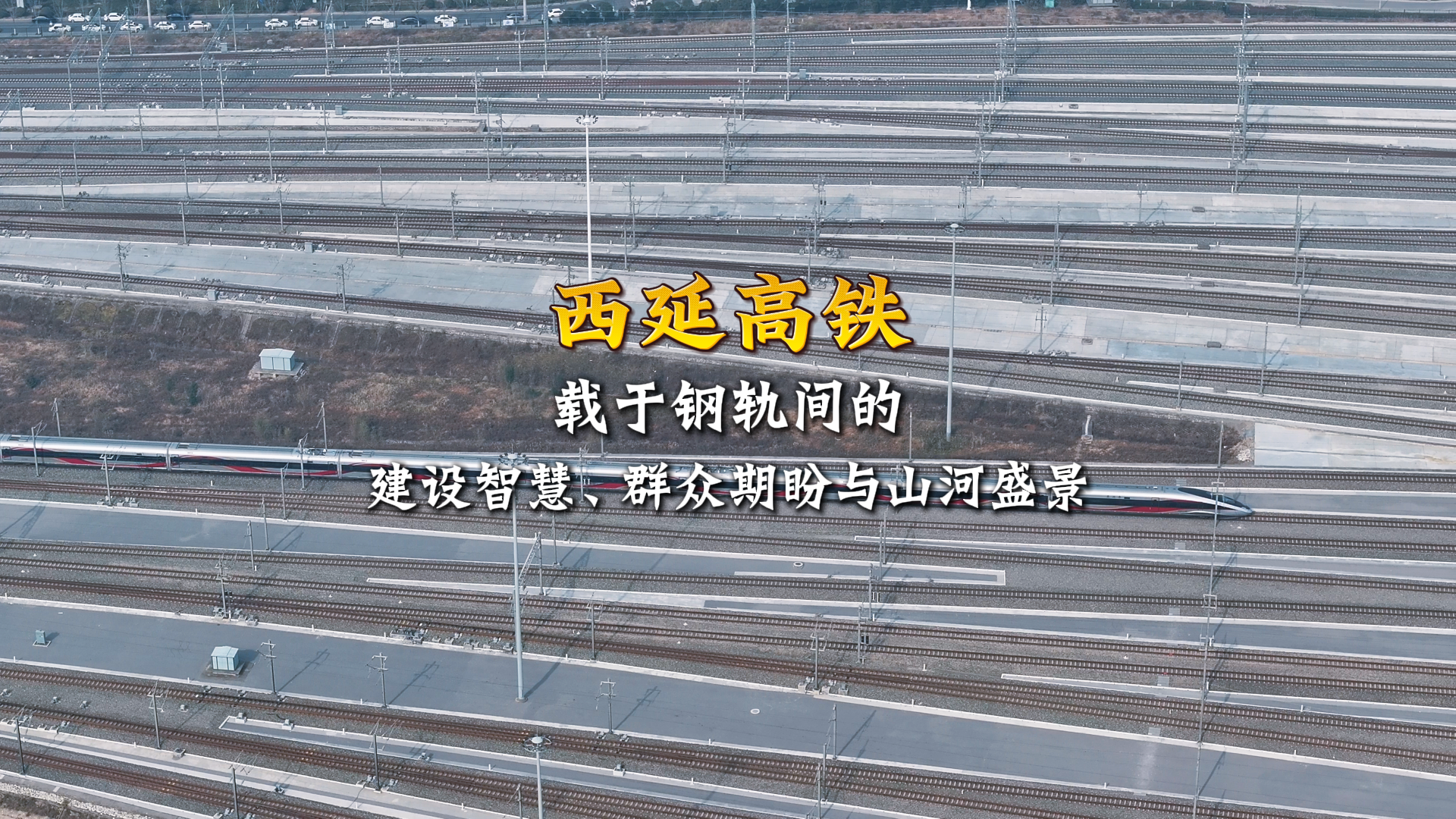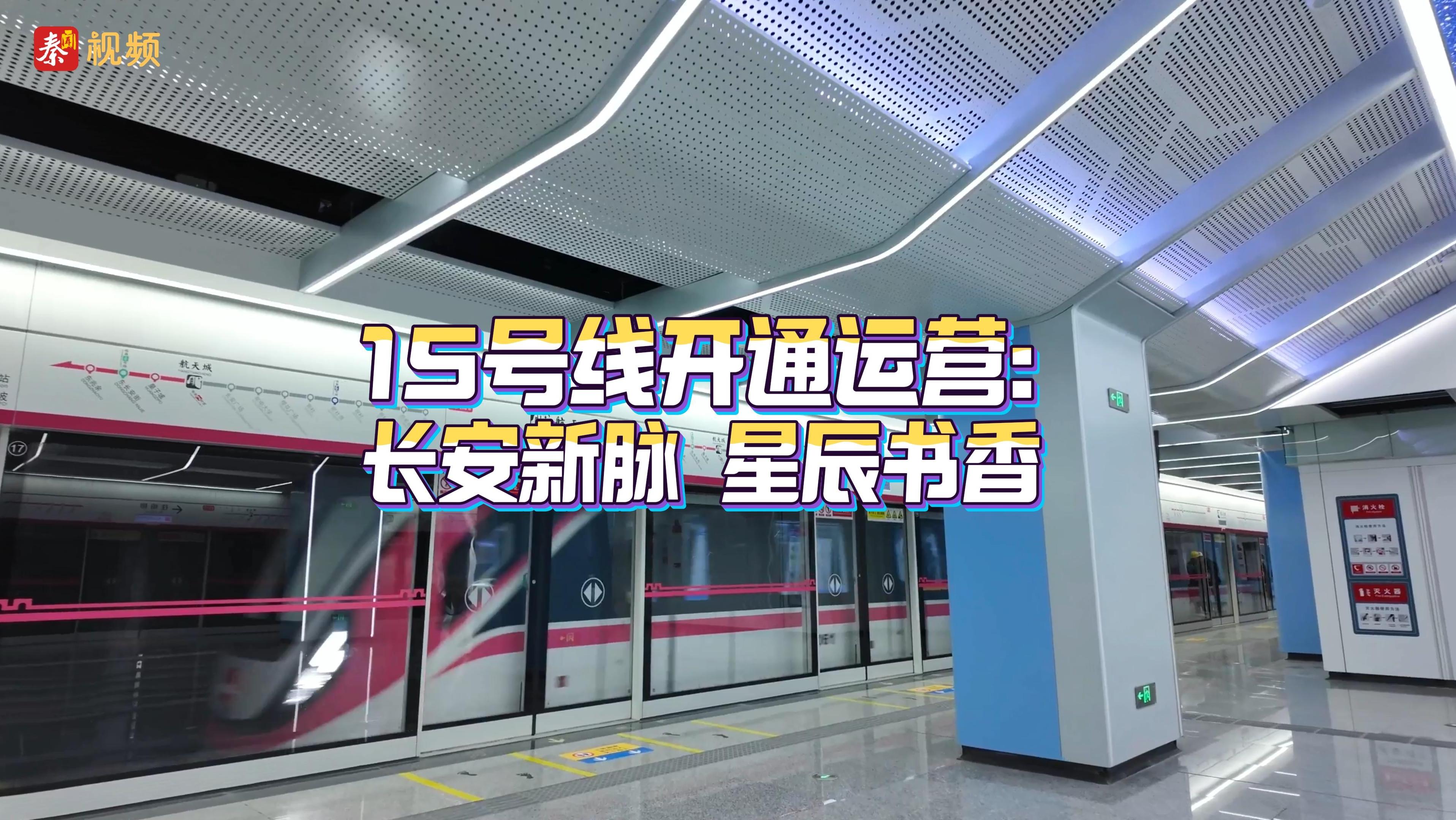■ 王帅许
日子在行色匆匆里日复一日碾过,心头时常盘旋一丝喧嚣中的落寞。高楼车流间,那份难以名状的寻觅感,总在热闹深处悄然浮现。
所幸,这落寞并非无处安放。那天,那丝难言的寻觅牵引着我的视线,不经意掠过街景时,马路对面一棵蓊郁梧桐的枝叶掩映里,静默立着一间老书屋。午后的阳光筛过叶隙,斑驳地落在它的木招牌上。岁月啃噬得边角模糊的木板上,“知旧”两个红字依然遒劲有力,透着一股沉静的底气。它敛着声息,含蓄温婉,等待着被有心人发现。
我推门而入,瞬间被一种熟悉而令人心安的气息包裹。陈旧纸张混合着淡淡灰尘,夹杂着老木头在时间里沉淀下来的气味,这股气息似乎瞬间稀释了马路对面传来的喧嚣,心头的焦躁也沉淀了几分。书屋不大,布局简朴。中间几块木板支起的展台,边角磨得光滑微亮,其上错落摆放着过期的杂志和厚厚的历史、军事类旧书。环绕四壁的老旧书架,漆皮剥落,却分门别类得极是清晰:历史、文学、传记、科技等标识虽褪色,却不失庄严。我素爱文学,便向文学区信步走去。
手指抚过一本散文集的书脊,又掂起一册薄薄的小说集。携书寻到角落一个矮小的马扎坐下,就此潜入另一个世界。那散文集如同一扇明亮的窗,推开它,清晰瞧见父母辈的生活场景:清苦却不乏筋骨的日子,朴素中闪烁着精神的微光。作者笔端流淌的不仅是记忆,更是对语言近乎虔诚的敬畏,字句间筑起的不仅是篇章,更是那个年代的气节。纸页间的烟火气与筋骨,竟让方才盘旋的落寞,找到了一个名为“对照”的支点,变得轻盈了一些。而那本小说集,如同递到我手中的一面镜,映照出作者年少时的跌宕:高中的青涩年华里,亲情、友情、懵懂的情愫,梦想与一次次碰撞的挫折……那些熟悉又陌生的片段,在我心上轻轻一撞,刹那间,沉寂的记忆池塘泛起涟漪,许多本以为模糊的面孔又清晰起来,带笑的、含泪的。
“就它们吧。”起身合上书页时,我才恍然发觉这书屋竟比初入眼帘时更为苍老。刚才沉浸于字句间未曾留意的“嘀嗒”声响,并非来自墙上的挂钟,它源于屋顶老朽的水管,冰冷的水珠不疾不徐地坠落,汇聚在桶底,悄然没过了接水处黯淡的金属箍沿。
柜台后戴着老花镜的店主,目光从镜片上方温和地望向我。结账的间隙,他轻抚着包书的旧报纸,告诉我“知旧”已有几十载春秋。说起这些年日渐稀少的脚步声,说起空落的展台,这旧书的营生自然越发冷清孤寂。“有时也想关掉算了。”他的声音平和,并未有太多波澜,只是眼角细密的皱纹在略显昏暗的光线里仿佛更深了些,“但年轻时就想开这样一间小书店,能守着这些老书。”他选“知旧”作名,正是企盼着寻得知音,能透过这泛黄变脆的纸页,触摸到往昔的温度。
书款付毕,脚步却在门口迟疑。再回望一眼这隐于城市一隅,与梧桐相伴的静默所在。一座城市,或许不能没有一片这样倔强伫立的老书屋,亦不能缺了这样一位甘于守望的情怀经营者。他们以阅尽千帆的姿态,在这喧嚣洪流中坚守着一方沉静,提醒步履匆匆的我们稍作停驻。在这慢下来的缝隙里,重新倾听那些唯有泛黄书页才能娓娓道来的古老故事。
门外梧桐枝叶轻轻摇曳,默许着这份古老书香的邀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