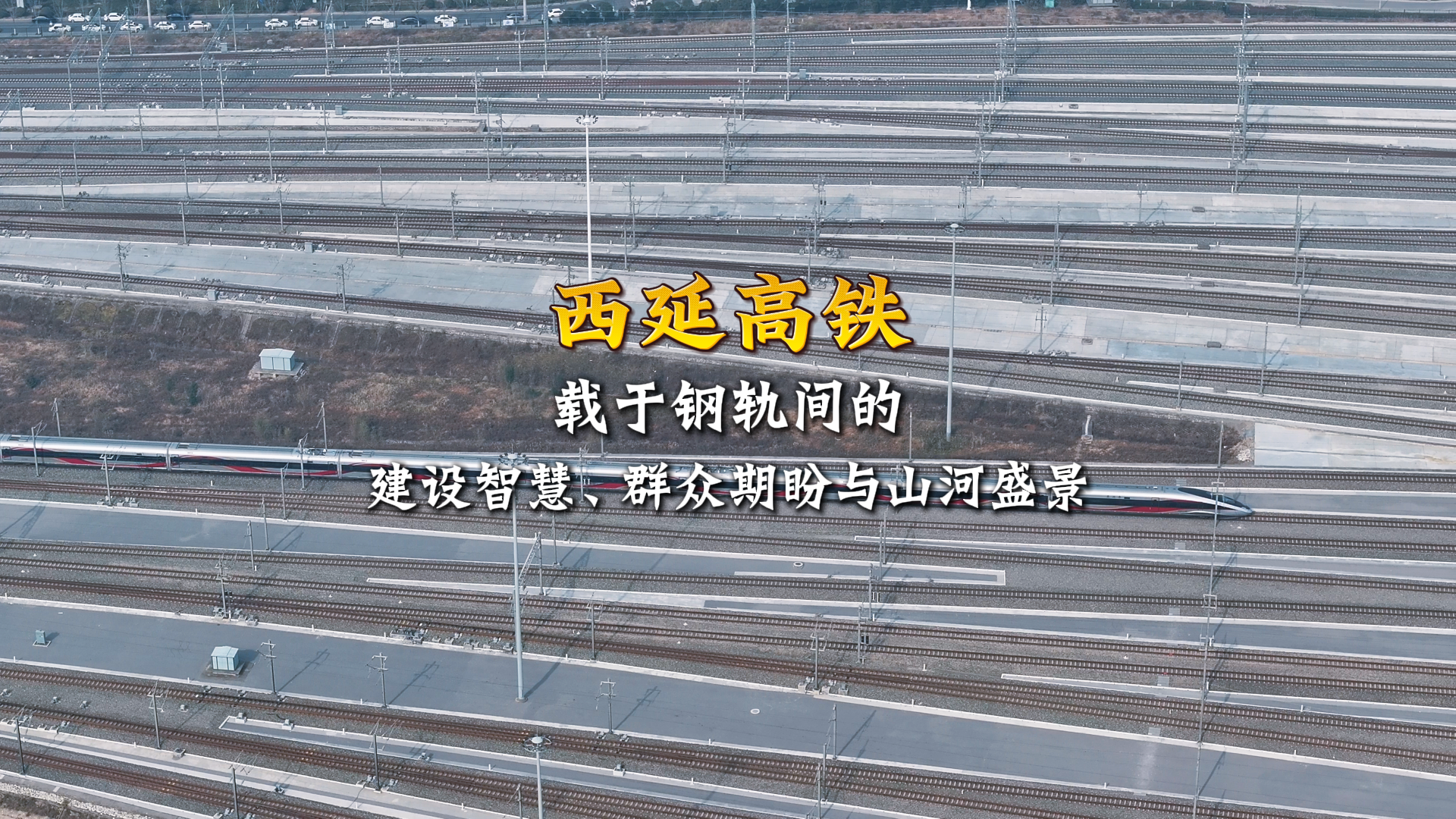■ 韩美荣
晨露还凝在柳梢头时,我已立在榆溪河岸边,准备开启新一天的晨跑。运动鞋踏过浸着潮气的塑胶跑道,踏步声惊飞了栖在水草上的蜻蜓。它们振着薄翅掠过水面,不经意间,便搅碎了满河流淌的晨光,漾开粼粼碎金。
三个月前,我却全然是另一副模样。那时我攥着衣角的手指微微发颤,望着蜿蜒如碧带的河岸,始终迈不出晨跑的第一步——在我眼里,这条常被露水浸润的跑道,仿佛比世间任何一条路都要漫长无际。
最初的晨跑,更像一场与呼吸的拉锯战。才跑出百十米,我的喉咙便像被砂纸反复研磨,每一次吸气都带着淡淡的腥甜与刺痛。胸腔里的心跳撞得肋骨咚咚作响,活像揣了只慌乱蹦跳的兔子。撑不过半里地,我就得扶着岸边的柳树弯腰喘气,额角的汗水滴落在地,惊得脚边的小蚂蚁倏地躲进草丛。有一回跑得太急,脚下一滑,我慌忙抓住一把柳树枝,却不料扯落了一串露珠。冰凉的露水顺着袖口往里钻,委屈瞬间涌上心头:何必这么跟自己较劲?
第二天,我悄悄关掉了闹钟,可身体却比闹钟更诚实——我还是按时起床,照常来到河边。这天我没敢快跑,只是沿着河岸缓缓前行。看晨雾像轻柔的纱巾,缠绕着成片的芦苇荡;听河水推着鹅卵石,发出咕噜噜的轻响,像是大地的呢喃。跑过前日的那棵柳树时,我忽然瞥见,曾被我攥过的枝丫上,竟冒出了一个嫩黄的芽苞,沾着上面的露水,在晨光里亮得像细碎的钻石。我忍不住笑了:连草木都在拼尽全力生长,我又怎能轻易停下脚步?
从那以后,我总爱在天刚泛鱼肚白时晨跑。彼时的榆溪河最是温柔,蓝盈盈的水面像一块被精心打磨过的美玉,岸边不知名的小草偶尔扫过脚踝,带来凉丝丝的痒意,挠得人心尖发颤。有一次,我遇见一位打捞河草的老汉,他见我跑得满脸通红,笑着喊:“姑娘,跑累了就歇会儿,这河边的风,比啥都解乏!”我放慢脚步,跑到芦苇荡旁吹风,再重新起步时,脚下竟轻快了不少。
晨跑的风景里,最动人的莫过于雨后的清晨。乌云刚被风卷走,河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雾,空气里满是泥土与青草的清新气息。我踩着水洼跑过木桥时,常有水鸟从芦苇丛中飞出来,翅膀划开雾气,身后便露出淡粉色的朝霞。跑着跑着,又会看见桥边的马兰花开得热闹,花瓣上的水珠坠入河面,漾开一个又一个小小的圆晕。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晨跑的意义,或许就藏在这些不期而遇的温柔里——是露水打湿的发梢,是马兰花的清芬,或是老汉随口的一句叮咛。
如今的我,早已能沿着整个河岸跑个来回。脚步踩在塑胶跑道上,轻重缓急都有了准头。呼吸也变得规律,吸气时能闻到水汽里混着的青草香,呼气时能听见自己的心跳。那心跳声伴着流水声,像是为我量身谱写的晨跑乐章。
现在,跑过河畔的柳树时,我也会停下来歇歇——看晨练的老太太甩着红绸子跳舞,看打捞河草的老汉弯腰劳作,看岸边的马齿苋慢慢舒展开叶片。跑完后,我还习惯掬一捧河水洗把脸,那凉意瞬间在鼻尖炸开,让人神清气爽。这时我总会想起最初那个站在岸边的自己,原来所谓的蜕变,不过是对每个清晨的坚持。
露水快干时,我便转身往回走,心里满是踏实。榆溪河的雾早已散尽,阳光铺在水面上,像撒了一把碎金子,晃得人睁不开眼。渐渐地,伴着河水的哗哗声,远处早市上忙碌的吆喝声也传了过来,那热闹的声音迎着阳光,渐渐变得清亮。
而我,也在这奔跑的晨光里,开启了属于自己的美好一天。